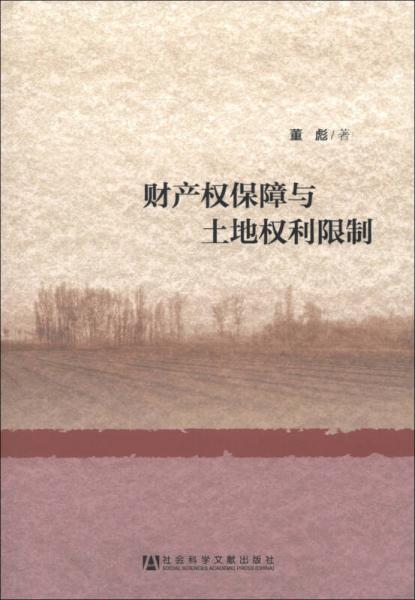财产权保障与土地权利限制
- 作者
-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3年4月 第1版
- ISBN 9787509743614
- 定价 79.00
内容简介
财产的价值在于利用,只有当财产权人能够自由支配该财产,对其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时,财产权对其才有实际意义。如果权力可以肆意介入私人生活,对他人财产权加以限制或剥夺,且不需要给予相应补偿,则财产权对权利人而言,并无实际价值。因而,作为通例,现代社会法治国家均注重对财产权进行保障。这一保障包括存续保障和价值保障两个方面。公权力对财产权进行限制时,亦应对此有所顾及。一般而言,对财产权的限制属于法律规范对于财产权内涵的确定,不侵犯财产权的本质内涵,是财产权人应当承担的财产权社会义务。原则上,对财产权进行限制时财产权人应当予以容忍。与一般财产相比较而言,土地承载着更多的社会功能,相应的,土地权利人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具体到制度和规范的层面,主要体现为土地所有权人或土地使用权人受到立法权或行政权的拘束。基于土地权利的社会义务性,国家有权对土地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进行合理限制,而土地权利人应当作出必要的牺牲。只有当该限制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构成过度限制,从而形成特别牺牲,事实上逾越了财产权社会义务性的界限时,土地权利人才能够获得补偿。对于如何规范过度限制土地权利乃至财产权的问题,不同国家或地区采取了不同方法。以德国为典型的国家或地区通常采取扩张征收的方式,将土地权利过度限制的情形纳入征收的范畴,要求国家在对土地权利人进行过度限制时应当对权利人予以补偿。在这一模式下,学者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征收与土地权利的合理限制。换言之,土地权利被限制到何种程度才会构成法律规定的征收?而以美国为典型的国家或地区则主要将土地权利过度限制作为一种独立的损失补偿类型,与征收补偿相并列。此时,学术研究的重点则转变为土地权利限制达到何种程度才需要对财产权人进行补偿的问题,即财产权社会义务与过度限制的界限问题。我国法学界对该领域缺乏必要的关注。究其思想根源在于:西方法治国家多接受过权利启蒙教育,市民社会、权利本位等观念深人人心:权利制度体系较为完备,权力的行使受到权利制约的幅度较大;人们对权力介入私人生活领域、限制土地权利的行为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主体对权利的需要要求对土地权利进行保护的范围不仅仅限定在“权利归属”的范围内,而且扩张及于“权利利用”的范围。而我国的国民权利意识以及权利保护体系的现状限制了主体对权利的需要。在私权主体因为典型的征收行为而导致财产权发生变动、造成财产权损失,都难于获得补偿或者难于获得公正补偿的情况下,对不剥夺其权利的过度限制行为自然不会有太多的权利主张。反过来,这种较低程度的权利需要又成为制约孕育更高层次的权利意识和构建更为完备的权利规范体系的瓶颈。深入研究土地权利限制及补偿的问题,探寻其理论基础及制度框架,是走向以权利为本、理性、自由的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因而,有必要对我国土地权利限制的问题进行体系化的研究,重视介于土地权利合理限制与典型征收之间的模糊地带,在坚持社会发展与权利保护相一致原则的前提下,对土地权利人的权利予以更为完善的保护。具体而言,在我国,应当采取狭义征收的概念,将土地权利过度限制作为一种独立的损失补偿类型;将特别牺牲作为区分土地权利社会义务与过度限制的标准,即在个别情形,土地权利人所受限制的损失程度逾越土地权利人应当忍受的社会义务的限度,构成特别牺牲,需要给予相应的补偿。唯有如此,才符合宪法保障财产权的意旨。
目录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