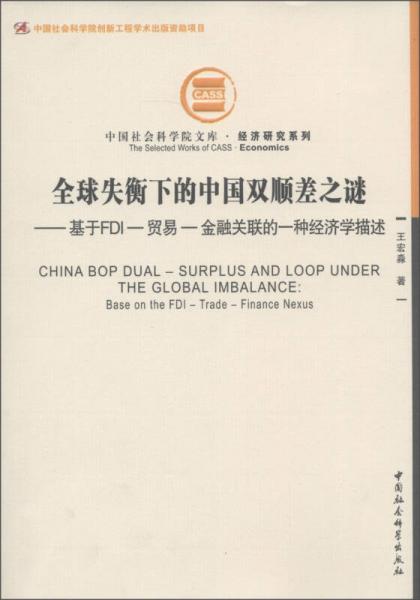全球失衡下的中国双顺差之谜:基于FDI-贸易-金融关联的一种经济学描述
- 作者
-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出版时间 2012年9月 第1版
- ISBN 9787516113912
- 定价 59.00
内容简介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出现了以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金融项目持续双重顺差、官方储备大规模对外金融投资为表征的外部失衡问题。数据表明,双顺差分别是由货物贸易顺差和直接投资顺差推动的。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经验角度看,这都是国际经济史上一种独特的现象。从时间上看,中国外部失衡的谜团迄今已持续了近20年,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大规模经常项目赤字为标志的“全球失衡”更是维持了整整一代人之久,国际收支的“古典自动调节机制”已经基本失灵了。这是因为,当代的“外部失衡”,除了国际货币制度等原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企业最优决策下的国际制造业转移与国内基本面因素结合所致,是一种长期现象。但由于传统的国际宏观经济学经典模型并不太关注FDI因素,这使得我们在分析中国双顺差问题时捉襟见肘。《全球失衡下的中国双顺差之谜:基于FDI-贸易-金融关联的一种经济学描述》试图将中国外部失衡之谜置于全球失衡背景下,通盘考虑“纵向”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FDI-贸易-金融关联和“横向”的欧美——中国——泛亚经济体的世界三角生产-贸易-金融关系,并结合中国的特殊情况将FDI和政策因素纳入宏观动态分析,进行一种理论上的新尝试,以图在较全面、细致解释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形成机制基础上,得出相应的政策结论。首先,企业最优跨国投资决策驱动下的微观“FDI-贸易关联”机制(FDI-TradeNexus)是理解全球失衡背景下中国“双顺差之谜”的一个起点。在全球化生产-贸易时代,在FDI流动与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一国所吸收的特定FDI形式(这与该国的特定国家特征有关)会影响到其贸易模式和平衡状况;而生产-贸易利益的获得又会反过来影响国际投资者的信心,进而影响FDI的进一步流入,并再次影响贸易(经常项目)。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在国际政治经济变化(外部推力)和中国自然禀赋条件、改革开放重大举措以及新重商主义政策(内部拉力)的结合下,FDI加速流人中国,并主要从事“垂直和出口平台型”生产-贸易活动,因而导致外资部门具有较高的净出口倾向,成为此后中国双顺差的发动机,外资企业行为在较长时间内主导着中国国际收支的方向。其次,随着外资流入,中国迅速形成了由内资部门、外资部门“两部门经济”以及在分割的两部门之间充当管理者、消费者和融资者的强力政府部门组成的特殊经济结构。因而内资部门和政府行为的影响也不能忽略。从内资部门看,由于中国政府的货币补贴,国有企业在改革最初出口增长较快,而在90年代后期以后由于出口退税、《对外贸易法》等政策因素的推动及内资技术进步,所以国内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净出口(顺差)增长迅速。在实际运行机理上,双顺差体现为中国经济内部和外部的“双重循环”,而政府行为在双顺差的内外双重循环中扮演了至为关键的角色。在经济转轨启动时,在外汇短缺和国内储蓄行政动员已到限度的条件下,中国政府为了获得初始的货币扩张机制来刺激经济增长,其中一个重要战略是通过引入FDI(同时限制短期资本外流)形成金融项目顺差,并给外资部门加工贸易税收政策等优惠,来保证FDI-贸易关联下外资部门的贸易(经常项目)顺差的实现;在固定汇率和结售汇体制的配合下,政府获得双顺差外汇储备的同时也意味着按比例发行国内货币;而这些增量货币则在政府利率管制政策下,经由国有银行信贷途径,对内资部门(特别是国有企业)提供融资和补贴(这又表现为“国际收支一货币金融关联”),内资部门资本积累和产出因而得以提高,保证了内资部门的经济增长率和贸易(经常项目)顺差。内、外资两部门的经常项目顺差和FDI流人的金融项目顺差,使得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为下一轮的货币扩张和经济增长提供了融资,从而实现了“FDI-贸易-金融关联”机制下的“双顺差内部循环”。如此机理,既需要同期国际外部需求扩大的必要条件,也需要国内政府通过制度供给,推行内外资两部门差异化政策来作为保证才能实现。但政府推行内外资差别政策的一个副产品,是造成内资、外资两部门之间出现因资本边际生产力、资本积累转化率(资本流动性)差异、内资和外资的资本收入税率差别而带来的极不对等的套利机会,而这种不均等的套利机会在两部门分割情况下是无法得到平滑的,于是大量国内资本先通过各种途径外流,然后披上FDI外衣回流(FDI迂回),以假外资形式实现制度性套利,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顺差。
目录
丛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经济研究系列— END —